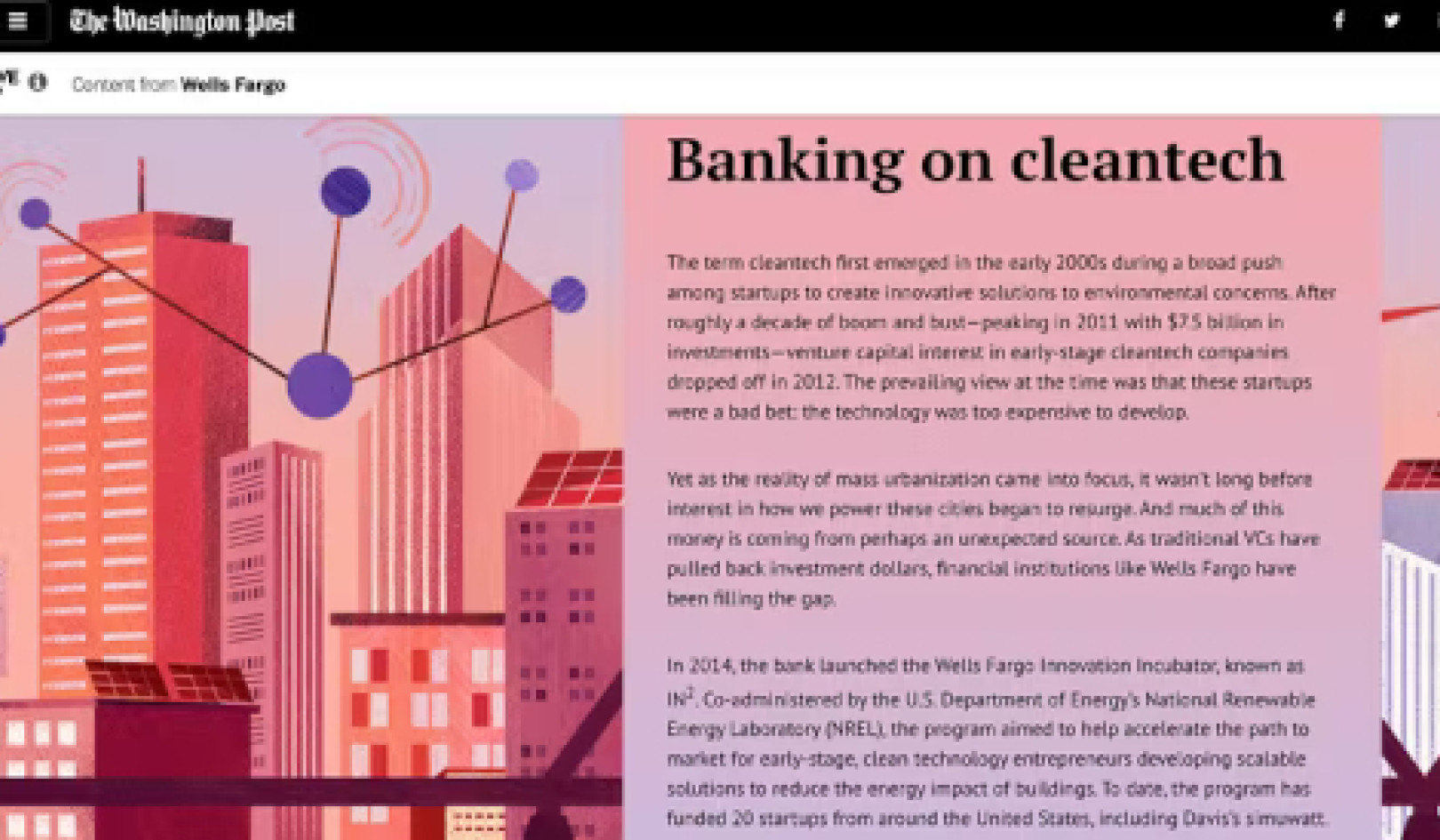虽然尚不清楚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对支撑当代生活的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冲击。
世界银行 估计 到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收缩8%至2020%,而COVID-19将使71-100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 在发达国家,人们对卫生,休闲,商业,教育和工作实践进行了重组(有人说是好的),以促进专家倡导和(有时是勉强地)由政府倡导的社会疏远形式。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COVID-19所做的更改的影响。 对于某些人来说,隔离期为沉思提供了时间。 当前我们社会的结构方式如何引发此类危机? 否则我们如何组织它们?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机会应对其他紧迫的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或种族主义?
对于其他人,包括那些被认为是脆弱或“必需的工人”的人,这样的反映可能反而是从更加内在的危险感直接产生的。 是否为诸如COVID-19之类的事件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是否在汲取了教训,不仅是在再次发生此类危机时处理此类危机,而且还从一开始就预防了这些危机? 恢复正常的目标是否足够,还是我们应该寻求重新改造正常本身?
这些重大问题通常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 当我们的常态意识破灭时,当我们的习惯被破坏时,我们就会更加意识到世界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人类有能力制定如此崇高的计划吗? 我们是否有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长期规划? 可能存在哪些障碍,也许更紧迫,我们将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以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作为来自三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工作考虑以各种方式参与针对意外事件(例如COVID-19)进行长期计划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工作审问了这些问题。 那么,人类实际上是否能够成功地为长期未来做好计划?
牛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我们对短期计划的痴迷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可能是可以克服的。 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紧急治理专家克里斯·泽布罗夫斯基(Chris Zebrowski)认为,我们缺乏准备,远非自然而然,是当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果。 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可持续发展转型专家Per Olsson反思了如何利用危机点改变未来–借鉴过去的例子,以学习如何在进入未来时更具韧性。未来。
我们是这样建造的
罗宾·邓巴
COVID-19强调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关键方面,这些方面看似无关,但实际上源于相同的基本心理学。 其中之一是从食品到卫生纸的各种商品的抢购和库存激增。 第二点是,当专家们警告政府多年来流行病迟早发生时,大多数州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是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 所有这三个因素都以相同的现象为基础:强烈倾向于在短期内优先考虑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众所周知,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动物都没有考虑到其行为的长期后果。 经济学家将此称为“公益困境”。 在保护生物学中,它被称为“偷猎者的困境”,也更通俗地说,是“公地的悲剧”。
{Vembed Y=CxC161GvMPc}
如果您是伐木工人,是应该砍伐森林中的最后一棵树还是将其保持原状?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动摇,森林最终将重新生长,整个村庄将得以生存。 但是,伐木工人的困境不是明年,而是他和他的家人是否能活到明天。 对于伐木者而言,实际上从经济上讲要做的是砍伐树木。
这是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您是否能够实现明天是绝对确定的。 如果您今天死于饥饿,那么未来就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您能度过美好的明天,那么事情可能会有所改善。 从经济上讲,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部分是我们过度捕捞,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的原因。
心理学家知道,支撑这一过程的是低估未来。 动物和人类 通常更喜欢 除非将来的奖励非常大,否则现在从小的奖励到以后的更大奖励。 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取决于额叶(额叶位于您的眼睛上方的大脑部分),其功能之一就是使我们能够抑制这种诱惑而无需考虑后果。 正是这个小小的大脑区域使我们(大多数人)有礼貌地将最后一块蛋糕留在盘子上,而不是狼吞虎咽。 在灵长类动物中,大脑区域越大,它们在这类决策中的表现就越好。
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可以设法生活在一个大型,稳定且相互依存的社区中的事实完全取决于这种能力。 灵长类社会群体是隐性的社会契约。 为了使这些群体能够在面对群体生活所必然产生的生态代价的情况下生存,人们必须能够为了自己的公平利益而放弃其他一些自私的愿望。 如果那没有发生,该小组将很快分裂并分散。
在人类中,无法抑制贪婪行为会很快导致资源或权力的过度不平等。 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国,这可能是内乱和革命的最普遍的单一原因 香港 !
同样的逻辑支撑着经济全球化。 通过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其他地方,本土工业可以降低成本。 问题在于,这是由于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来支付现在家庭工业中多余的雇员,直到他们找到替代就业为止,这对社区造成了损失。 这是一个隐性成本:生产者没有注意到(他们可以卖得比以前便宜的多),而购物者没有注意到(他们可以买到便宜的)。
有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 自然的社会世界 规模很小,几乎没有村庄大小。 一旦社区规模扩大,我们的兴趣就会从更广泛的社区转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社会错综复杂,但正如所有历史帝国所发现的那样,社会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越来越脆弱的组织,有继续分裂的危险。
企业提供了这些影响的小规模示例。 富时1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为 急剧下降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四分之三在短短30年内消失了。 幸存下来的公司是具有远见的公司,对快速致富的策略不感兴趣,这些策略不会使投资者获得最大的回报,也没有社会效益。 那些已经灭绝的企业主要是那些追求短期战略的企业,或者由于规模庞大而缺乏适应性结构灵活性的企业(请考虑度假经营者)。 托马斯库克).
 我们自然的社会世界几乎没有村庄大小。 罗伯·柯伦/ Unsplash, FAL
我们自然的社会世界几乎没有村庄大小。 罗伯·柯伦/ Unsplash, FAL
最终,很多问题都会缩小。 一旦社区超过一定规模,其大多数成员就会变得陌生:我们失去了对他人的个人和社会所代表的公共项目的承诺感。
COVID-19可能会提醒许多社会,它们需要重新考虑其政治和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更接近其本国的局部化形式。 当然,这些肯定需要合并联邦上层建筑,但是这里的关键是自治社区级政府的水平,公民认为他们在事情的运作方式上有个人利益。
政治的力量
克里斯·泽布罗夫斯基
就规模和规模而言,它没有比里多运河大得多。 伸展 全长202公里,加拿大的里多运河被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壮举之一。 该运河系统于1832年开放,旨在作为通往连接蒙特利尔和金斯敦海军基地的圣劳伦斯河重要河段的替代补给路线。
该项目的推动力是在美国,英国及其盟国之间发生战争之后,与美国人继续敌对的威胁。 来自1812-1815。 尽管运河永远不需要用于预期的目的(尽管成本高昂),但这只是人类的机智与巨大的公共投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威胁。
 里多运河的一部分,托马斯·伯罗斯(Thomas Burrowes),1845年。 ©安大略省档案馆
里多运河的一部分,托马斯·伯罗斯(Thomas Burrowes),1845年。 ©安大略省档案馆
“折现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习惯。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如何 大脑是有线的 或我们灵长类祖先的悠久遗产。 我们对短期主义的倾向已经社会化。 这是我们今天在社会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方式的结果。
企业优先考虑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利润,因为它吸引股东和贷方。 政治家不赞成长期项目,而希望采用快速解决方案来保证即时结果,这种解决方案可以在每四年发布的竞选文献中找到。
同时,我们周围有很多风险管理工具的例子,这些工具非常复杂,而且往往资金充足。 重大的公共工程项目,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庞大的军事组织,复杂的金融工具以及精心设计的保险政策,支持了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证明了我们有能力为未来作计划和做好准备的能力。
近几个月来,公众对应急准备和响应系统在管理COVID-19危机中的至关重要性。 这些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它们使用视线扫描,风险记录,备灾演习和多种其他专业方法来识别和计划未来的紧急事件。 此类措施可确保我们为将来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即使我们不确定何时(或是否会)实现这些事件。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COVID-19的爆发规模,但之前在亚洲爆发的冠状病毒意味着我们知道 一个潜在可能。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警告过 国际流感大流行 多年了 在英国,2016年国家防灾项目“运动天鹅座”明确表明: 该国缺乏能力 充分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危险已经明确识别。 众所周知,为这场灾难做准备。 缺乏在这些重要系统上提供足够投资的政治意愿。
在许多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紧缩的逻辑)促使许多关键服务(包括紧急情况准备)的资金被削减,这是我们安全与保障所依赖的。 这与包括中国,新西兰,韩国和越南在内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对准备和响应的承诺确保了 快速抑制 疾病及其对生命和经济的破坏力降至最低。
尽管这样的诊断可能首先看起来很暗淡,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在其中找到希望。 如果造成短期主义的原因是我们组织方式的产物,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重组自己以解决它们。
最近的研究表明,公众不仅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而且认识到 要求紧急行动 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生存危机。 我们不能允许COVID-19的死亡和毁灭是徒劳的。 在这场悲剧发生后,我们必须准备彻底地重新考虑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社会,并准备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来确保我们物种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我们不仅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流行病,而且还具有更大的规模(也许并非无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威胁将要求我们在面对未来威胁时行使人类的远见和审慎能力。 这样做并非超出我们范围。
如何改变世界
佩尔·奥尔森
尽管在流行病分析中出现了短期主义和结构性问题,但那些关注长期研究的人一直认为这是变革的时候了。
COVID-19大流行导致许多人争论说这是 千载难逢的时刻 进行转化。 这些作家说,政府的回应必须推动 深远 与能源和粮食系统有关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否则我们将来将容易受到更多危机的影响。 有些人进一步声称 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而不再痴迷于增长和消费。 但是同时转换多个系统并非易事,值得更好地了解我们对转换和危机的了解。
历史向我们表明,危机确实确实创造了独特的变革机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如何使荷兰的汽车社会过渡为自行车国家。 在能源危机之前, 对汽车的反对日益强烈,并出现了一场社会运动,以应对日益拥挤的城市和与交通有关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儿童。
 骑自行车是荷兰的主要交通方式。 杰斯与阿芙森/未飞溅, FAL
骑自行车是荷兰的主要交通方式。 杰斯与阿芙森/未飞溅, FAL
另一个例子是黑死病,这是14世纪席卷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瘟疫。 这导致了 废除封建制度 以及加强西欧的农民权利。
但是,尽管可以从危机中产生积极的(大规模)社会变革,但后果并不总是更好,更可持续或更公正,而且有时出现的变革因环境而异。
例如,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影响了亚洲运行时间最长的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两次叛乱 非常不同。 在前者中,斯里兰卡政府与分离主义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由于自然灾害而深化和加剧。 同时,在亚齐省,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分离主义者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其中一些差异可以用冲突的悠久历史来解释。 但是,不同群体准备进一步推进议程,应对危机本身的方式以及在海啸发生后的行动和策略也有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变革的机会可以被自私自利的运动抓住,因此可以加速非民主主义的趋势。 不希望提高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团体之间可以进一步巩固权力。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在菲律宾和匈牙利等地。
由于有许多人呼吁变革,因此讨论的余地是变革的规模,速度和质量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成功应对这种重大变化所需的特定功能。
人们通常会混淆哪些行动实际上会有所作为,现在应该做什么以及由谁来做。 这样做的风险是,错过了由危机创造的机会,而凭借最好的意图和创新的承诺,努力只会回到危机前的状态,或者略有改善,甚至导致危机。根本更糟。
例如,有些时候抓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改变金融部门,但最强大的力量将系统推回了类似于崩溃前的状态。
造成不平等,不安全和不可持续实践的系统不容易转变。 顾名思义,转型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例如权力,资源流动,角色和惯例。 这些转变必须发生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上,从实践和行为,到规章制度,再到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涉及到改变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COVID-19期间,现在至少在原则上致力于此类变化的努力,曾经被视为激进思想的想法现在已由许多不同的小组采用。 在欧洲,绿色复苏的想法正在增长。 阿姆斯特丹市正在考虑实施 甜甜圈经济学 –旨在提供生态和人类福祉的经济体系; 和 普遍基本收入 正在西班牙推出。 所有这些都在COVID-19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进行了试点,但是这种大流行使火箭助推器成为了现实。
因此,对于那些寻求利用这次机会创造改变以确保我们社会的长期健康,公平和可持续性的人们,有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 剖析危机的根源并相应地调整行动至关重要。 此类评估应包括以下问题:发生何种类型的多重危机,相互作用的危机,“现状”的哪些部分真正崩溃,哪些部分牢牢固定在哪里以及谁受到所有这些变化的影响。 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确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准备就绪”的试点实验。
处理不平等现象也很重要 包括边缘化的声音 避免转型过程被一组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所支配和选择。 这也意味着尊重并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的竞争价值观合作。
我们如何组织努力将定义未来几十年的系统。 危机可以是机遇,但前提是要明智地应对危机。
作者简介
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实验心理学系进化心理学教授, 牛津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讲师Chris Zebrowski 英国拉夫堡大学以及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研究员Per Olsson, Stockholm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