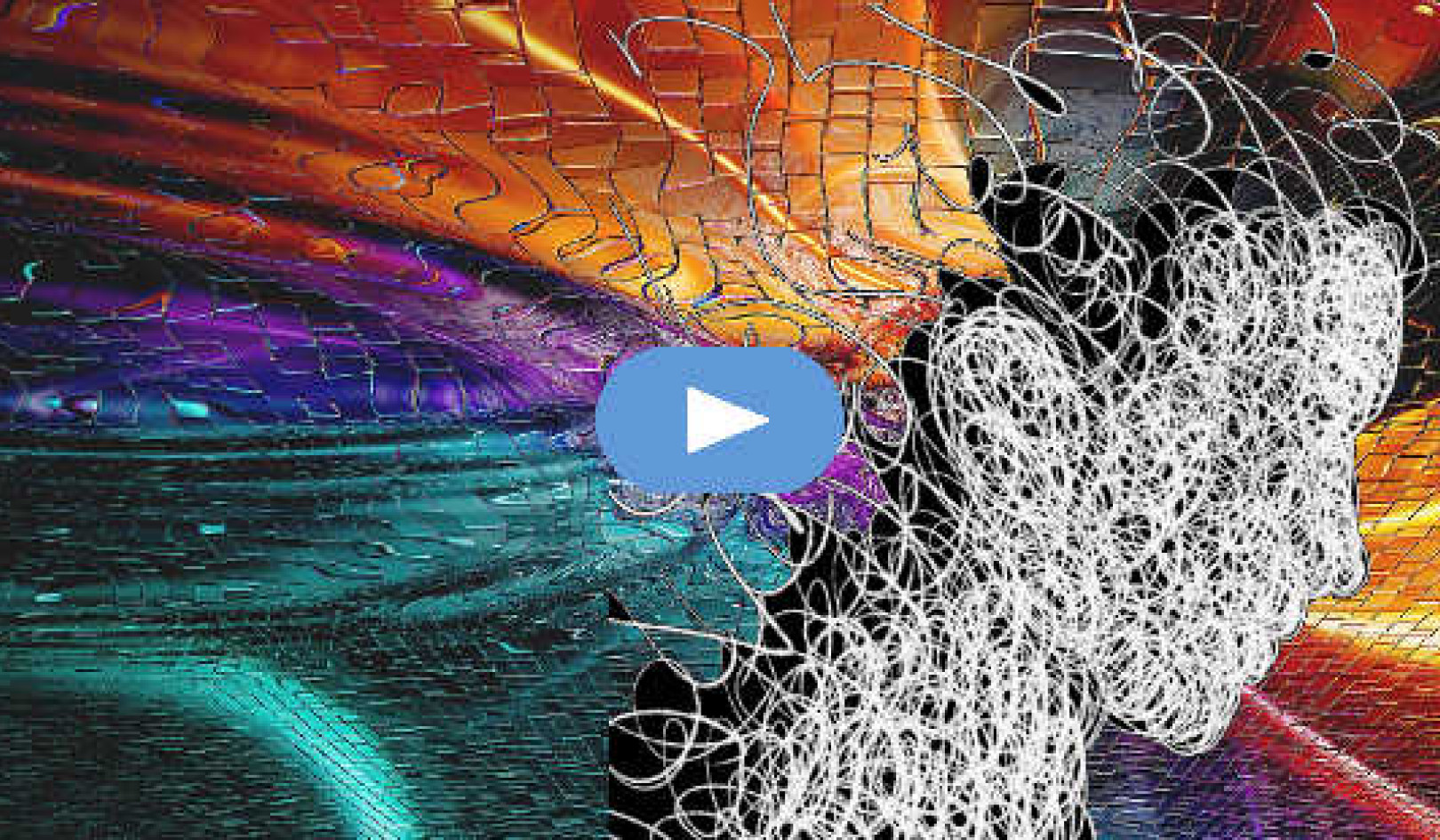图片由 Pexels
多年来,我认为我的超额成就、完美主义和对控制的需求是为了证明我已经足够好——成为最好的、完美的,是最重要的。 仅由 “足够”的方式。 但是与一位直觉教练的会面带来了一些别的东西——我需要完美,这样我才能成为 安全。 如果我能做到完美,那么我将无可非议,不受批评或任何形式的惩罚。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来说明如何 不安全 即使是很小的选择也可能在我家。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我正准备去教堂。 我穿上了一件衣服,我决定想看看我的白色紧身衣不穿内衣是什么感觉。 我妈妈发现了我的所作所为,大怒,决定要为此“打屁股”。 这意味着我必须进入我父母的房间,从腰部以下脱光衣服,在我父母的床上弯下腰,然后忍受被我父亲的皮带扣在我光秃秃的臀部和大腿上,直到打我的人感觉好些为止。 这就是我好奇穿紧身衣不穿内裤是什么感觉的回应。
这就是我控制一切的疯狂欲望的来源。 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会遭到如此暴力的对待。 如果我有 任何 想到我会因为做出那个选择而被打败,我当然不会 考虑 它——更不用说,做到了。 为了给自己一种安全的错觉,我不得不试着找出做某事的“正确”方式,并确保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 右 办法, 每周 时间。
当然,孩子应该怎么知道呢? 没有办法知道。 这种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会激怒我的父母并导致殴打——是我家成长过程中基本动力的核心:恐惧。
恐惧完美 合理的 响应
虽然我们经常说恐惧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但恐惧是一种完美的 合理的 对我家环境的反应。 爸爸会明确地利用我们对他的恐惧来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移动得不够快或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会解开腰带并迅速将其从裤子上的环中拉出来,这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嗖 声音——我们会跑得像地狱一样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以避免挨打。 直到今天,我听到那个声音时都害怕得抓紧,肚子不舒服。
因为我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尽量不挡道,这意味着我花了很多时间独处。 当我七岁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栋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 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两户人家,我的父母把它改回了一个家庭。 孩子们住在楼上的公寓,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我的厨房是厨房,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有一个可以工作的水槽、炉子和冰箱——这对于玩“房子”来说非常棒。
那个房间成了我的避难所。 我一有机会就退缩了。 我喜欢阅读,并且会连续几个小时沉浸在书籍中。 我们小时候有很多书,但我花了太多时间阅读,以至于我很快就读完了,所以我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相同的书。 我们有几本我喜欢的关于神话、传说和童话的大书。 我还把“小房子”的书读了很多遍,以至于我把所有的段落都背下来了。
我在房间里感觉相对安全,阅读把我带到了更快乐的地方,就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来说,一个更快乐的家庭。 独自一人在我的房间里也让我更容易“退房”,因为珍妮和我来称呼它。 当事情对我们来说太多了,我们就会去其他地方,精神上。
成年后,当我们恳求父母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在他们拒绝时试图与他们分手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家人就像 加州旅馆: “你可以随时‘退房’,但你永远不能离开。”
在家庭之外,我的恐惧给了我一种“冷漠”的品质。 不是我没有朋友,而是我一直是那种只有一两个知心朋友,其余的更像熟人的人。 我可以在一个团体中有效地进行社交——例如,我通过在合唱团唱歌或制作音乐剧而结交的朋友——但我非常谨慎。 再加上我在学业和音乐方面的成功,很多人都认为我“自闭”。
事实上,我只是害怕。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到成年,人们常常认为我傲慢自大。 这就是我仍然使用“Ronni”的主要原因——我哥哥给我起的绰号,他小时候不会说“Veronica”。 我认为我的名字很漂亮,甚至在我离开大学时尝试开始使用它。 但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正式的名字,它增强了人们认为我“固执己见”的倾向——所以我继续使用“Ronni”,这样人们就会觉得我更友好、更平易近人。
恐惧:坚定的伴侣
我说过,我所经历的恐惧是对我的家庭环境的理性反应——确实如此——但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恐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害怕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在我不断的恐惧和实现目标的动力之间存在着一场持续的战斗。 但恐惧往往胜出,因为我开始害怕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失败——数百万人可以做的事情,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典型的例子是当我长大到可以接受驾驶培训的时候。 我曾是 确信 我将无法通过课程。 我试图告诉自己我很可笑,但我无法摆脱无法成功度过难关的感觉。 我终于开始寻找我认识的特定人,他们比我大一岁,他们已经拿到了驾照。 我想,“好吧——这些人设法做到了。 你也可以。” 我仍然没有完全相信。
当我开始恢复过程时,我被迫认识到恐惧一直是我一生中坚定不移的伴侣。 令人震惊的是,我确实一直生活在对几乎所有事物的恐惧之中。
只有他们的痛苦才重要
家庭中不健康的情绪动态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我的父母清楚地传达了这一点 其 疼痛很重要。 尤其是我的母亲,总是很快就对我们的痛苦不屑一顾,她说:“我从来没有 意思 伤害你,”好像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没有受到伤害。
可能是我在 XNUMX 岁时完全内化了我的痛苦并不重要这一信息的最明显例子。 不知从何而来,我的一个后臼齿开始受伤。 起初,这是一种钝痛。 我尝试服用阿司匹林来缓解疼痛,但它变得更糟了。 疼痛会在半夜把我吵醒。 我祈祷上帝会消除痛苦。 我起身服用了更多的阿司匹林。 我在半夜在地板上走了几个小时,捂着下巴,哭着——乞求减轻痛苦。
在我终于告诉我妈妈之前,我这样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 她带我去看牙医,六周前我刚看过牙医进行清洁。 他错过了一个(到目前为止)非常糟糕的腔。 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口腔外科医生,他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牙齿上的神经出奇地接近表面。 他说我需要根管,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完成了。
当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令人震惊,除了我对我的牙医在我之前的访问中错过了蛀牙感到失望。 直到我 30 多岁的恢复过程中,我才想起这一集,并想,“天哪! 我怎么没去找妈妈 立即地?! 我是在 多么痛,我说 没什么。 该 无法想象 如果我的女儿很痛苦,她不会来找我的!” 那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完全内化了我的痛苦无关紧要的信息。
他们的情感需求
在其他方面,我父母的情感需求是主要的。 这是一团乱七八糟的忠诚度证明,以及总是不断变化的规则,以至于你永远无法成功地满足它们。
成为一个期望不断变化的家庭的一员,既可怕又令人迷惑。 没有办法保证安全。 没有验证。 成为成年人提供 没有缓解。 只有更多的努力和持续的痛苦,因为你永远不会达到目标。 绝不。
当我现在看到这些模式时,很明显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寻找我永远不会得到的验证。 这是让人们与你保持联系的一种功能失调的方式。 父母应该清楚地告诉孩子他们没事。 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帮助他们的孩子培养强烈的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爱着,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安全的。
当孩子没有得到这个,当他们被虐待时,他们会不断地回来,希望他们最终能取悦他们的父母,并收到他们足够好的信息。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摆脱恐惧和功能障碍的一生
试图解除一生的恐惧和功能障碍是一项非常缓慢的任务。 当我第一次去 Al-Anon 时,他们告诉我,“如果你需要 30 年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你需要 30 年才能放松它。” 那不是好消息。 显然,我刚刚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艰苦跋涉,所以我努力为一路上的小胜利感到高兴。
例如,有一天,我女儿三四岁的时候,她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等我给她煮果汁。 我站在水槽边,想把冷冻的浓缩果汁罐摇到水罐里,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加水了,但它拒绝出来。 我开始更用力地颤抖,最后那块顽固的雪泥随着一声啪的一声飞了出来,让我身上布满了紫色的斑点。 刹那间,一连串脏话涌入我的脑海,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它们说出来。 下一秒,女儿笑得歇斯底里。 我立刻就知道她是对的——这个 是 有趣的。 如果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会笑的。 然后我发现自己和她一起笑。 我深吸一口气——小小的胜利。
尝试在旧唱片中加入新的凹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毅力,而且有很多次我试图做“正确”的事情——以一种平静、耐心的方式回应——而我却在翻唱里面。 有一天,我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地毯。 我当时五岁的女儿想帮忙。 坦率地说,我不想让她帮忙。 我只是想完成工作。 但我知道一个好妈妈会让她帮忙,所以我给了她把手,往后退了一步。
真空吸尘器几乎和她一样高,她把它推来推去——徒劳无功,但兴高采烈。 “我在帮你,妈妈!” 她对我咧嘴一笑。 我笑了,但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的时候,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 这是一个完全,过分,荒谬的反应,但我真的认为我可能会身体爆炸。 我设法隐藏了这一点,她可能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帮助”了她,然后她将真空吸尘器还给了我。 她非常高兴,幸福地没有意识到我的感受,但我想,“我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么小的事情谁会这么生气??”
与控制的迫切需要作斗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并按照我的时间表完成——感觉就像一颗炸弹在我体内爆炸。 后来,我意识到,我能够交出真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这是一个进步——又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做个好妈妈的愿望
回想那些年,最突出的是我想做一个好妈妈的愿望。 我想变得有爱心、善良、耐心。 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她很重要,她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她值得我尽最大努力,为了成为我能做的最好的妈妈,我必须成为我能做的最好的人。
她也是我决定与父母断绝联系的驱动因素。 我下定决心,她不会受到曾经伤害过我的相同动力的伤害。 我希望她快乐健康地成长。 但切断联系并没有提供彻底的情感休息,也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保护我的女儿。
当我第一次告诉她我们必须停止与父母见面时,她才六岁,她很难理解。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她出现了一些行为问题,我相信这与休息有关。 对她来说,我的父母很爱她,他们代表着乐趣和礼物。 她看不到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休息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女儿一直在闹,然后跺着脚冲到她的房间里大喊大叫。 我坐在楼梯上抽泣着,心想:“我这样做是为了 保护 她从痛苦中,她 仍然 痛苦!” 这真的让我怀疑我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
感觉 Waaaay 更糟了……
恢复的最初几年往往很困难。 有很多挑战,比如应对我的感觉 waaaay 比我想象的更糟。 有时,它是压倒性的。 还有这种没有人看到的巨大的内心斗争,有时我为自己感到难过。 我觉得我所做的所有辛勤工作都没有得到“荣誉”,因为只有我知道它正在发生。
有太多的恐惧——意识到我一直生活在多大的恐惧中——现在害怕我永远不会“正常”,以至于我是“损坏的货物”。 所有的恐惧都在前面和中心。 然后我的大任务变成了移动 通过 害怕。 感觉就像是一场孤独而隐秘的斗争。
康复几年后,当我女儿大约 8 或 9 岁时,我对她说:“我是你认识的最勇敢的人。” 我真的觉得我是。 这段康复之旅要求我重新审视我的整个生活,认识到我被严重虐待的时间,并感受到与创伤相关的痛苦——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第一次。
我也试图将那些新的凹槽切入旧唱片中,为自己创造健康的模式, 和 以确保我为女儿打破了循环。 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不断努力。 即使对于普通人来说,做新事物也总是需要冒险。 但对于那些在虐待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可怕的。
你从过去知道的可能是“坏的”,但它是熟悉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很舒服。 这意味着努力学习、成长——无论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是改善他人的生活——都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对于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离开熟悉的人的舒适,不能保证它会实现或值得,是可怕的。 但我愿意尝试。 赢、输或平——这让我勇敢. ——罗尼·蒂切诺
版权所有2022。保留所有权利。
经作者许可印刷。
文章来源:
书: 治愈从我们开始
治愈从我们开始:打破创伤和虐待的循环并重建兄弟姐妹关系
作者:Ronni Tichenor, PhD 和 Jennie Weaver, FNP-BC
 治愈从我们开始 这是两个不应该成为朋友的姐妹的故事。 Ronni 和 Jennie 在一个有着成瘾、精神疾病和虐待问题的家庭中长大,这些问题产生了不健康的动态,并且经常使他们相互对抗。
治愈从我们开始 这是两个不应该成为朋友的姐妹的故事。 Ronni 和 Jennie 在一个有着成瘾、精神疾病和虐待问题的家庭中长大,这些问题产生了不健康的动态,并且经常使他们相互对抗。
在这本书中,他们讲述了他们童年经历的原始真相,包括他们之间发生的虐待。 当他们走向成年时,他们设法走到一起,制定了一条让他们能够治愈他们的关系的道路,并打破代际创伤和虐待的循环,建立自己的家庭。 利用他们的个人和专业经验,他们提供建议来帮助那些希望从自己痛苦的成长中得到治愈的人,或者治愈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或订购此书, 点击此处。 也可以作为有声书和Kindle版本使用。
作者简介

 Ronni Tichenor 拥有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专攻家庭研究。 Jennie Weaver 在范德比尔特护理学院获得学位,是一名获得董事会认证的家庭护士从业者,在家庭实践和心理健康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验。
Ronni Tichenor 拥有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专攻家庭研究。 Jennie Weaver 在范德比尔特护理学院获得学位,是一名获得董事会认证的家庭护士从业者,在家庭实践和心理健康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验。
他们的新书, 治愈从我们开始:打破创伤和虐待的循环并重建兄弟姐妹关系 (Heart Wisdom LLC,5 年 2022 月 XNUMX 日)分享了他们从痛苦的成长过程中治愈的鼓舞人心和充满希望的故事。
了解更多 心与灵魂姐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