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在童年后期,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的社会是一个鲁莽的轨道上。 我记得在平淡的唯物论和商业化的美国1950s被激怒了。 正如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历史,我开始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的crassness和愚蠢的战争。 人们为什么让他们的政府,像校园恶霸? 地球的命运似乎是白痴的呓语的手。
同时,它是明确的,世界是在变化的旋风:每年带来的新产品和新发明(如激光和微波炉),(如周围民权运动的人)的社会争议,文化现象(像披头士)。 它是所有令人振奋,但令人不安。 唯一肯定被改变本身和它正朝着什么是更多,更大,或更快的领导大方向。
在1964我的高中地理老师,她经常到类的讥讽旁白,提到一些有关将跟随,如果美国在东南亚的冲突得到陷入可怕的后果。 当时,我的意义不大重视她的警告:亚洲意味着我没有更多的比一本书的文字和图片。 仅仅几年后,我这一代中最年轻的男子,无论是在越南或拼命想找到一种方式,以避免被派往那里。 我是一个幸运儿:我有高的选秀抽签号码,从来不叫。 相反,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反战运动。
越南战争是一个对于我们许多人的教育 - 从一个非常不同的教育,我们在学校接受。 我们的教科书使我们相信,美国是最明智和最善良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自由的火炬手。 然而,在越南,我们的政府似乎要倡导傀儡独裁和漠视人民的意愿。 战争似乎是非常军工复杂的创造,艾森豪威尔,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对警告 - 巨大的跨国公司,主要是由五角大楼的合同资金,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有兴趣在原材料,市场和利润;和经常摧毁土著世界各地的文化,以充实自己。
面具脱落
一旦在越南的辩论已撕开的文明帝国的文化,在我们生活的面具,我们许多人开始看到,这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不公平。 很明显,例如,习惯于被污染和枯竭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妇女和有色人种被经常利用丰富不断增长的富裕和贫者愈贫。 这是任何年轻的人很难吸收信息。 怎么办呢?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宗教家庭,我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精神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也许人类的自私,残忍,和短视的方式行事,因为它需要的启示。 在心脏的最严重的工业污染或政治恐怖的邪恶在我心中存在过,我想,如果仅在本质上。 如果我不能抹去嫉妒,仇恨,贪婪,从我自己的灵魂,然后我没有指责别人的缺点的真正基础,但如果我可以的话,那么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
未来二十年,我研究佛教,道教,和神秘的基督教精神的社区生活;并探讨了新时代哲学,治疗和培训。 这是一个成长和学习的时间,我将永远感激。 但最终我意识到,灵性世界的问题是不完整的答案。 我经常遇到人的奉献上帝是不容置疑的,但通过了一个独裁的或不容忍的态度,或掩盖了经济和社会困境,在他们的灵气的世界观背景下,不能轻易诬陷。 经过二十年的等待形成一个“临界质量”开明的先锋带头成为一个普遍和谐的新时代人类的进化,我开始认识到,在现实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
同时我比较宗教学的调查,导致我对部落社会的研究 - 如那些为母语的美国人,非洲人,澳洲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 这些非工业的人民,其中许多人有古老的地球上的精神传统,做(至少,直到接触时间)份额第一世界的许多问题。 他们的文化可能一直不完善,在他们自己的方式 - 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人,例如,经常进行人的牺牲 - 但他们在对环境的破坏性方面远远低于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毁灭性。 他们的生存模式是可持续的,而我们没有。 正如我研究部族人民,很明显,我认为他们的社会和生态稳定性不只是从他们的宗教,而是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派生。
现代世界疯狂
同时,我开始看到现代世界的精神错乱,不只是由于缺乏道德或精神的认识,但嵌入在我们的集体存在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的可怕的战争,和整个第三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第一届世界城市贫困的蔓延不能完全停止通过政府调控这里有一个新的发明。 他们是在我们所采取的总体格局存在固有的。
我渐渐看到,我们吃什么,我们如何思考和生活,和我们所使用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意味着一定的合同或与自然的约,每一种文化使这样的公约,其成员(大多是无意识)遵守。 人类与自然存在于一个互惠的平衡:正如人们塑造自己的需要的土地,土地和气候变化也影响着人们 - 带领他们不仅依靠本地和季节性的食品,但招待对待生活的态度,从他们那年春天通过生活模式。 沙漠牧民往往有一致的和可预见的神话,社会组织形式,世界观,不管他们住在大陆,同样可以对沿海渔民,猎人北极和热带园艺说。 此外,历史的事后和跨文化的比较表明,与自然的一些公约是比别人更成功。
文明的控制
文明 - 生活模式,包括城市,分工的一生,征服,和农业 - 代表一个独特的剥削的公约,在人类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环境控制和减少其约束在他们自己。 在过去,许多文明已下降,因为他们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土壤,水,森林在其身后留下的沙漠。 目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社会,其对自然的依赖模式的出现将导致类似的两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已成为在全球,我们可能会严重损害整个地球的生物活力,我们的机构终于溅射和死亡。
一路上,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提出了异议:难道你不只是浪漫化的原始文化? 如果你确实离不开现代生活的便利,你可能会苦不堪言。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地返回到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方式。 我们不能“uninvent”汽车,核反应堆,或计算机。 这声音,拒绝闭嘴。 有时出现无可辩驳的论据。 但至今,它已提供替代解决方案 - 我们文明的伟大潜在的危机正在主持一个全球生物大屠杀的事实是,我们。 “现实主义”的声音,只是说,危机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一个渐进的必要性。
但有替代品,当然,也有解决方案。 远离我们的掠夺性电子工业文明的路径不需要企图模仿原始人lifeways的。 我们不可能都成为Pomos。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什么已经忘记了在“进步”三月得多。 我们可以恢复的责任一直被称为土著人民的土地和生活感。 即使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所有细节后的科举文化,我们至少可以说,总体来看,讨论过程中,它可能会应运而生,并采取实际步骤,朝着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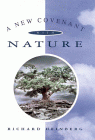 本文摘自:
本文摘自:
与自然的新的盟约
理查德Heinberg。
©1996。 再版发行的权限,任务书, http://www.theosophical.org.
信息/订单。
关于作者
理查德Heinberg广泛演讲,广播和电视上出现,并撰写了大量论文。 他的替代每月痛批,MuseLetter,被列入最佳替代通讯在乌托读者的年度清单。 他也是作者 庆祝冬至:地球的季节性变化规律,通过节礼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