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童年后期,我才开始意识到周围的社会正走在一条鲁莽的道路上。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种乏味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让我怒不可遏。随着我对历史了解的加深,我开始把战争视为粗鄙和愚蠢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人们会允许他们的政府像校园恶霸一样行事?地球的命运似乎掌握在一群疯子手中。
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都有新产品和发明(例如激光和微波炉)、社会争议(例如围绕民权运动的争议)以及文化现象(例如披头士乐队)涌现。这一切令人兴奋,却也令人不安。唯一确定的只有变化本身以及它朝着更大、更多、更快的方向发展。
1964年,我的高中地理老师在一次她惯常的讽刺挖苦中提到,如果美国深陷东南亚战火,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时,我并没有把她的警告放在心上:亚洲对我来说不过是书本上的文字和图片而已。仅仅几年后,我们这代的大多数年轻人要么身在越南,要么拼命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我是幸运儿之一:我的征兵抽签号码很高,所以从未被征召入伍。相反,我上了大学,并加入了反战运动。
越南战争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但这与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我们的教科书让我们相信,美国是最睿智、最仁慈的国家。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火炬手。然而在越南,我们的政府似乎在拥护一个傀儡独裁政权,无视人民的意愿。这场战争似乎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最后一次演讲中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的产物——这些庞大的跨国公司主要依靠五角大楼的合同获得资金;它们日益掌控政府政策;它们只对原材料、市场和利润感兴趣;并且为了自身利益,它们肆意摧毁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
面具脱落
当越南战争的辩论撕开了我们所生活的帝国文化的文明面具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化充满了各种矛盾和不公。例如,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在污染和耗尽自然环境;妇女和有色人种经常遭受剥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对于任何年轻人来说,这些信息都难以接受。我们该怎么办?
由于我成长于一个宗教家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从精神层面寻求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或许人类之所以自私、残忍、目光短浅,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启迪。我想,即便只是本质上,最恶劣的工业污染者或政治恐怖分子心中的邪恶,也存在于我的心中。如果我无法从自己的灵魂中根除嫉妒、仇恨和贪婪,那么我就没有资格指责他人的缺点;但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或许我可以树立一个榜样。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研习佛教、道教和神秘基督教;居住在灵修社群中;探索新时代哲学、疗法和训练。那是一段成长和学习的时光,我将永远心怀感激。但最终我意识到,灵性并非解决世界问题的全部答案。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却抱持着专制或不宽容的态度,或者对那些难以用他们虚无缥缈的世界观来解释的经济和社会困境视而不见。在等待了二十年,期盼着一批开明的先驱者能够引领人类进化,迈向一个普世和谐的新时代,然而,我开始意识到,现实中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
与此同时,我对比较宗教学的研究逐渐将我引向对部落社会的研究——例如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的部落社会。这些非工业化的民族,其中许多拥有古老的、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传统,(至少在与人类接触之前)并没有面临许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文化或许在某些方面并不完美——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曾定期进行活人献祭——但就环境破坏性而言,他们远不及二十世纪的工业化社会那样具有破坏性。他们的生存模式是可持续的,而我们的则不然。随着我对部落民族的研究不断深入,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和生态稳定性不仅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源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现代世界的疯狂
与此同时,我开始意识到,现代世界的疯狂并非仅仅源于道德或精神意识的缺失,而是根植于我们集体存在的方方面面。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发动的骇人战争,以及贫困在第三世界和我们自身发达国家城市中的蔓延,都无法仅靠政府的某项法规或某项新发明来彻底遏制。它们根植于我们所选择的生存模式之中。
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饮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我们使用的资源种类和数量,都蕴含着与自然的一种契约或盟约,而且每一种文化都与自然缔结了这样的盟约,其成员(大多是无意识地)遵守着这些盟约。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状态:正如人们根据自身需求改造土地一样,土地和气候也影响着人们——这不仅促使他们依赖当地和当季的食物,也促使他们形成源于自身生存模式的生活态度。无论生活在哪个大陆,沙漠牧民往往拥有连贯且可预测的神话体系、社会组织形式和世界观;沿海渔民、北极猎人和热带园艺者亦是如此。此外,历史的回顾和跨文化的比较表明,某些与自然缔结的盟约比其他盟约更为成功。
文明的控制
文明——这种包含城市、终身劳动分工、征服和农业的生活模式——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剥削性契约,在这种契约中,人类力求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对自身的限制。历史上,许多文明因其对土壤、水和森林不切实际的需求而衰落,留下了沙漠。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其对自然的依赖模式似乎正将我们引向类似的结局。但这一次,由于我们的文明已遍及全球,在我们自身的制度最终崩溃消亡之前,我们或许已经严重损害了整个地球的生物生存能力。
一路上,我脑海中一个声音不断反驳:你难道不是在美化原始文化吗?如果真的要放弃现代生活的所有便利,你肯定会痛苦不堪。再说,我们不可能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取消”汽车、核反应堆或电脑的发明。这个声音始终萦绕不去。有时,它的论点似乎无可辩驳。但迄今为止,它并未就我们文明面临的巨大根本危机——我们正在主宰一场全球性的生物大屠杀——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现实主义”的声音只是说,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进化的必然。
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也有解决办法。摆脱我们这种掠夺性的工业电子文明,并不意味着要模仿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都变成波莫人。但我们可以重新学习在“进步”进程中被遗忘的许多东西。我们可以重拾土著民族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对土地和生命的责任感。即便我们现在无法设想后帝国主义文化的全部细节,至少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谈论它,探讨它可能形成的进程,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实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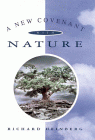 本文摘自:
本文摘自:
与自然的新契约
作者:理查德·海因伯格。
©1996年。经出版商Quest Books许可转载。 http://www.theosophical.org.
信息/订购书籍。
关于作者
理查德·海因伯格曾广泛举办讲座,多次出现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并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创办的另类月刊《缪斯信笺》(MuseLetter)曾入选《乌特尼读者》(Utne Reader)年度最佳另类通讯榜单。他也是以下著作的作者: 庆祝冬至:通过节日和仪式来颂扬地球的季节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