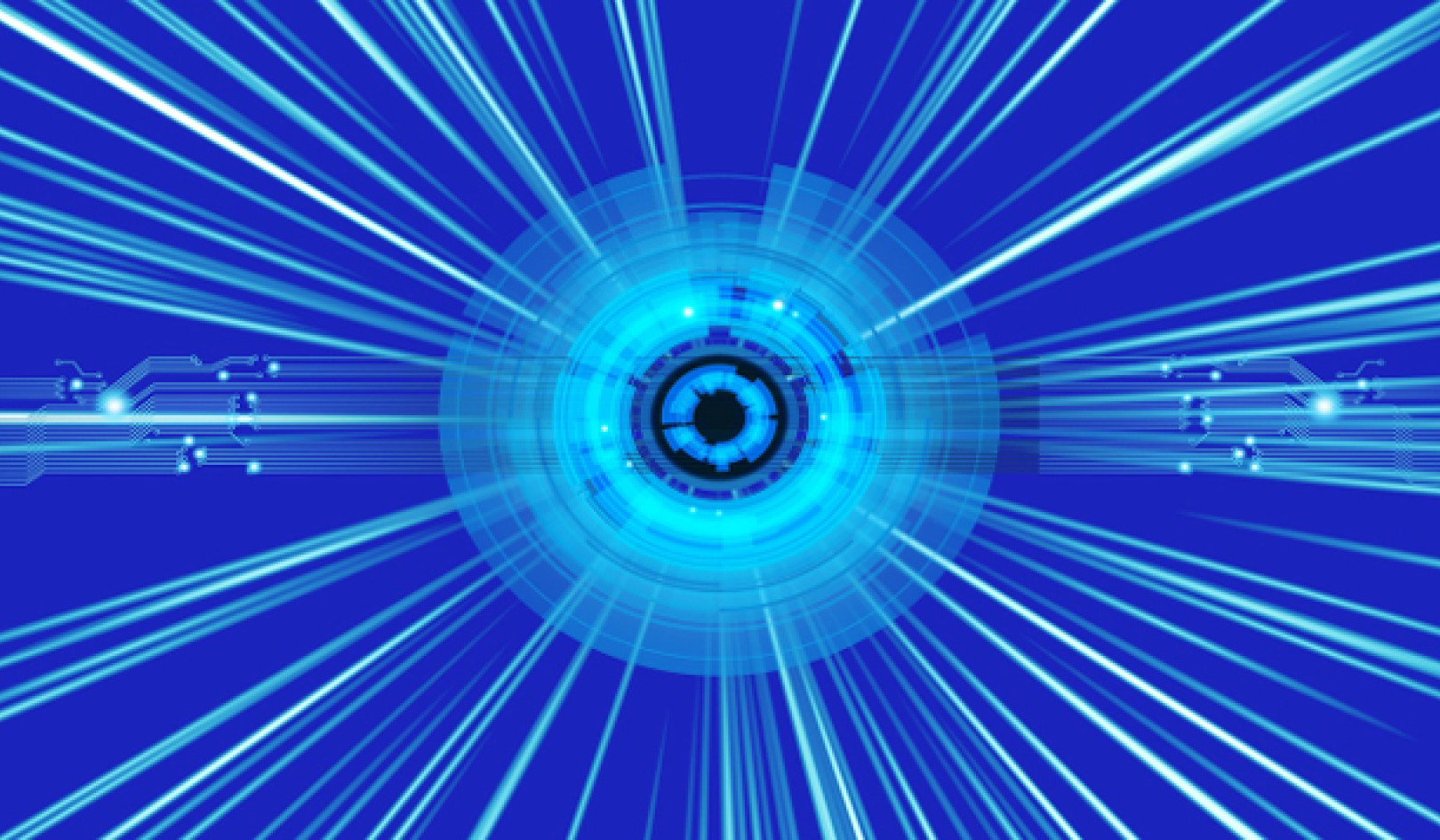在1970s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母亲的支持很少。 存在Shutterstock
在1970s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母亲的支持很少。 存在Shutterstock
在过去几十年的澳大利亚生活中,政府政策逐渐为职业母亲提供更多支持,特别是通过儿童保育补贴和育儿假。
但是,是什么促使澳大利亚父母在工作和育儿方面做出选择?
我采访了几代澳大利亚母亲,了解他们选择的护理和有偿工作的组合,以及原因。 结果显示我们谈论工作家庭的方式存在巨大差距。
虽然我们的公开辩论仍然在理性和经济方面陷入困境,但母亲们将其决策过程描述为情绪激励。
1970s:对职业母亲的支持很少
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母亲的支持很少。 1970s引入了托儿服务,以支持劳动力 妇女的参与但是,职业母亲仍然被认为是有争议的。
莎莉的故事
莎莉和她的丈夫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978之后将这一天分成两半,分享有偿工作和平衡责任:
...因为我是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当孩子刚刚六周大的时候我就回去了。 [...]我上半场教学,他早上和宝宝在一起。 我回到家,乳房充血,准备喂养,然后他会在下午和晚上去上课。
但莎莉对于她是否应该和她的孩子在一起感到矛盾,并回忆起对工作母亲和儿童保育的态度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议。
1980s:导航育儿短缺
在1980s的工党政府下扩大了儿童保育服务,并通过了立法 促进女性就业。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母亲在参与劳动力方面面临着持续的障碍,特别是缺乏满足其需求和愿望的儿童保育。
Hazel的故事
Hazel的进步雇主让她休产假,并在现场提供托儿服务。 虽然她觉得别人在孩子年幼时工作,但她意识到维持她产前的职业生涯对她的情绪健康很重要:
我很早就意识到,你知道你的世界合同[...]当我回到工作岗位时我并没有想过多休假,即使这是一个玩杂耍[...]有人曾对我说过:快乐的妈妈,快乐孩子,当我担心重返工作岗位时。 特别是我的岳母对此非常非常批评。
吉纳维芙的故事
Genevieve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离开了她的广告工作,因为她觉得“母亲是一个有价值的角色”和“一份值得尊重和平等地位的工作”。 但是她觉得有些人认为女性只是“呆在家里”,并认为专业的儿童保育优于母亲照顾:
那种难过,'孩子们喜欢它! 他们受到了刺激! 他们在家里很无聊! 他们拥有所有这些玩具,而且他们正与其他孩子交往,这真是太棒了。 我已经这么多年了。
1990s:引入育儿假
育儿假被引入1990的联邦奖励,该奖项的父母是 无薪休假 宝宝出生后。 在1990s中,澳大利亚人对母亲是否应该从事有报酬工作以及孩子是否应该从事儿童保育这一看法 好坏参半.
凯特琳的故事
Caitlyn生活在一个小型的地区小镇,她说,当她第一次出生在15的1991月份时,她觉得自己有回归有偿工作的评价:
那时的儿童保育似乎是一个肮脏的词。 这里没有儿童保育中心,而且你会把你的孩子整天留在别人的照顾下,这几乎让你成为一个糟糕的父母,因为你在逃避你的责任或什么......
凯瑟琳的故事
即使在大城市,选择也是有限的。 当凯瑟琳的伴侣的兼职工资无法支付他们的开支时,她不情愿地在她的孩子三个月大时回到有偿工作。 面对当地中心的漫长等候名单,她发现附近有一位提供家庭日托服务的女士: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针对一个女人,她可能并不完美,但她是他们的人,你知道,这不是一个机构。
在1990s结束时,儿童保育仍被视为妇女的私人责任(和问题)。 澳大利亚的母亲越来越多地从事家庭以外的有偿工作,但在政策环境不一致的情况下,她们仍在继续努
2000s:新的儿童保育补贴
在2000引入的新税收福利安排中,霍华德政府授予在职父母每周为每个孩子提供50小时儿童保育补贴的权利,而未领薪的父母可以申请24小时。
- 27%担心成本问题
- 22%无法在首选中心获得一席之地
- 20%无法获得所需的时间
- 18%无法在正确的位置找到服务。
时间使用调查显示,母亲通过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来管理这个不可能的玩杂耍,因此政策支持不足的负担落在他们身上 而不是雇主或孩子.
克里斯汀的故事
克里斯汀在2009度过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并决定在她最小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前不回到有偿工作岗位。 在她的职业女性中产阶级郊区,这一决定让她感到社会孤立:
我有一个做了预期事情的朋友,十二个月后又回去工作[...]她非常紧张,回去工作,我通过做出决定让自己免于压力和焦虑作为一个母亲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良心[...]哲学上,对我来说,母性很容易 -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与很多朋友完全不同......
2010s开始:更多支持,但情绪复杂
从2007到2013,工党政府改革了儿童早期教育和护理的意图 建立劳动力参与,因而生产力。 为2011的主要照顾者引入了政府资助的产假,并在2013中引入了父亲和伴侣假。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许
Rowena的故事
Rowena决定在看完自己的母亲与全职工作并且感到持续内疚和紧张的情况下,在她的母亲身边兼职工作:
...如果我有幸生孩子,我想专注于你知道拥有它们,没有别的东西真正重要。 比如,人们认为他们在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每个人都可以替换。
改变我们谈论儿童保育的方式
这些记录反映了澳大利亚母亲的各种各样的经历,但在他们的叙述中有一致的线索。 大多数母亲希望与母亲前的身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感受到对社会有意义的贡献感,并享受与子女的关系。
如果政府不理解母亲选择不同支持的原因,那么家庭政策的效力就会受到限制。 劳动力参与和经济生产力是政府政策的合理目标,但它们本身并不充分。
忽视孕产妇和儿童福祉同样重要的目标可能会加剧围产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高发率。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女性会问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选择母亲,当你的社会不能充分支持这种选择时?
关于作者
Carla Pascoe Leahy,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DECRA研究员, 墨尔本大学
相关书籍
at InnerSelf 市场和亚马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