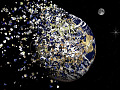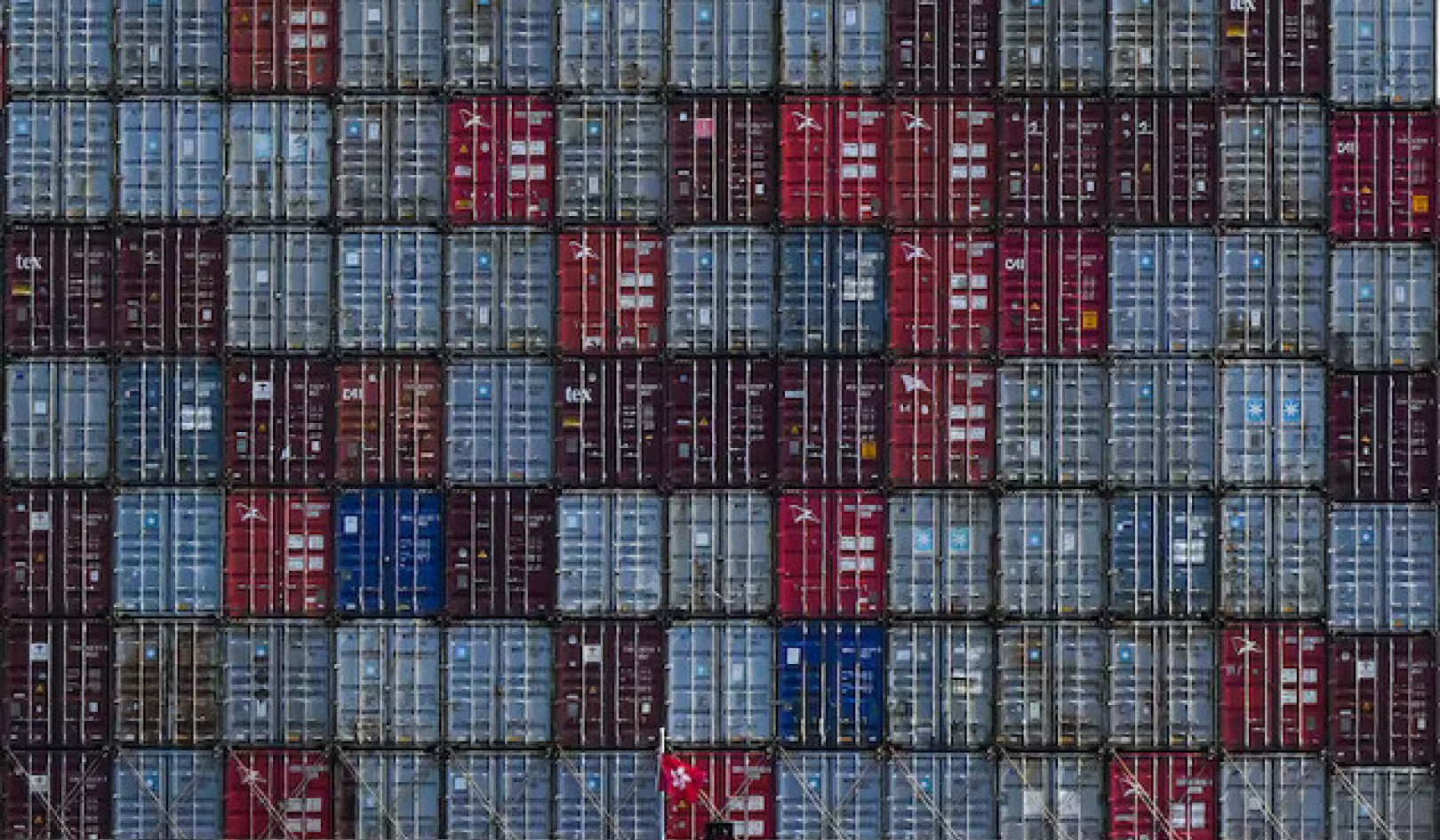澳大利亚监狱人口迅速增加。 通常认为这是由于犯罪增加所致。 尽管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挖掘得更深,但这一联系远不那么清楚。 一个国家使用监禁的程度实际上似乎更多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而非必然性。
维多利亚的监狱系统 过去两年经历了特别惊人的过分拥挤。 越来越多的人被判处监禁。 更多的人被拘留,而不是被允许保释。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拒绝假释,因此将他们的全部监禁服刑。
各国政府认为,犯罪率正在上升,社区感到恐惧,因此更多的罪犯必须被送入监狱。 假释人员可怕的高调罪行也导致了假释的关闭。
事实上,犯罪率不以任何统一的方式增加。 该 最新数字 维多利亚,在那里监禁率大幅上升,在某些罪行(包括一些但不是所有的暴力犯罪)节目的增加和某些犯罪减少,而大部分保持稳定。
监禁的增加不仅仅是对犯罪增加的回应。 犯罪和判刑之间的时间间隔排除了监狱人口近期增加(例如威慑)导致犯罪率稳定的说法。
所以犯罪率并不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监禁。 这个结论是通过向澳大利亚以外寻求证明的。
全球犯罪和监禁图片
指某东西的用途 监禁在世界各地 差别很大。
例如,美国著名的禁锢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囚犯698 100,000每人口)更多的人口。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使用的监狱这样的速度(如丹麦67 / 100,000,瑞典57 / 100,000)的十分之一左右,与英国在144 / 100,000。 该 最新的ABS数据 把澳大利亚的监禁率定在190 / 100,000,但是上涨很快。
同时,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犯罪率有所不同 - 但并不是与监禁率相关的。 例如,整个发达国家的犯罪率从1970s到1990s显着增加。 但在那个时期, 迈克尔·托尼表演 美国和荷兰的监禁率显着上升,加拿大和挪威的监禁率保持稳定,法国的监禁率在芬兰和日本急剧下降。
实际上,监禁率和犯罪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研究 Tapio Lappi-Seppala表演例如,一些国家的监禁率与犯罪率一致(如美国,丹麦,德国和日本),而在其他国家则相反(如英国,意大利,荷兰和新西兰)。
正看着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关于监禁政治的知识 芬兰的经验。 在1960s政府决定减少监禁的使用,以使芬兰更加符合其他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在1960和1990之间,芬兰的监禁率从165 / 100,000下降到60 / 100,000。 这个 是通过例如减少监禁可用的罪行,缩短刑期,增加提前释放计划,引入社区服刑,并严格限制年轻罪犯获得监禁条件。
A 芬兰评论员 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改变的政治意愿。 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 社会和政治共识 在一个不受短选举周期推动的政治体系中,政府寻求和接受关于替代形式的惩罚的专家独立意见。
但是,这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当时芬兰没有小报记者; 犯罪不是一个“热键”问题 用于出售报纸。
虽然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相比,芬兰大幅度降低了监狱的犯罪率,但犯罪记录的趋势和速度却是如此 在所有这些国家类似。 从1950 2010到犯罪率在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均匀上升,并行高达约1990,然后趋于稳定或有所下降。 在瑞典,丹麦和挪威监狱率,但是,相似和稳定,而芬兰监狱率大幅下降。
如果犯罪率不要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检测值 许多 评论员 将监禁的不同使用与更广泛的政治框架和社会不平等程度联系起来。 他们指出,新自由主义国家 - 如美国和澳大利亚 - 往往有更高的监禁率,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社会民主国家的监禁率则较低。
相关的解释集中在一个国家是否有包容性或排他性政治。 这是有争议的 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监狱率最高,因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导致对异常公民的“排他性文化态度”。 相比之下,欧洲社团主义社会(“协调市场经济”)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社会 据说:
将违法者视为需要再社会化,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链接也可以做 一国的福利制度和监禁率之间:福利减少与监禁增加相关。 日益增长的惩罚性政策与美国和英国福利国家的倒退之间的联系常常被注意到。 美国是最高的 收入不平等水平 西方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低。 斯堪的纳维亚也排名 最高的社会支出 在欧洲。
监禁是一个政治选择
民主的形式也可能对政治和社区对惩罚的态度很重要。 一些评论员(见 点击此处, 点击此处, 点击此处 和 点击此处)比较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对抗性的两党民主国家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更加共识驱动的民主国家。
有人认为,多数派的两党制往往会引起对抗和惩罚性的法治秩序政治。 相比之下,基于共识的决策模式被认为是妥协的优先考虑,使对立的矫正政治不太可能。
显然,监禁的使用程度是政府的政策选择。 环顾世界,现在广泛认识到犯罪率和监禁率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监禁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之间有更明确的联系。
如果犯罪率不要求更多地使用监禁,我们必须立即重新考虑我们急于过度监禁的情况。 如果我们从国际比较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将会在学校,家庭和社区投资更多,而监狱则更少。
![]()
关于作者
 Bronwyn Naylor是莫纳什大学的副教授,在加入维多利亚州法律改革委员会之前曾担任律师,然后在莫纳什大学法律系任职。 她是莫纳什大学卡斯塔人权法中心的副主任,《替代法杂志》的编辑兼委员会主任和成员,维多利亚州罪犯关怀与重新安置协会(VACRO)的董事会成员。
Bronwyn Naylor是莫纳什大学的副教授,在加入维多利亚州法律改革委员会之前曾担任律师,然后在莫纳什大学法律系任职。 她是莫纳什大学卡斯塔人权法中心的副主任,《替代法杂志》的编辑兼委员会主任和成员,维多利亚州罪犯关怀与重新安置协会(VACRO)的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