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辞去了高中教师兼校长的工作,这份工作让他身心都得到了滋养。他放弃了这份热爱,为了养家糊口,在纽约那个鱼龙混杂、黑手党横行的服装区当起了服装制造商。
他后来后悔了这个决定,因为它使我们全家陷入了严重而漫长的危险之中。但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只知道,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下午晚些时候回家,而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回家。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总是尽可能熬夜,门铃一响,我就冲到门口,扑进他张开的双臂里。那一刻的喜悦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仿佛被保护和被爱包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粗糙的胡须拂过我娇嫩脸庞的感觉。尽管他工作到很晚,但他每周都会抽出一天时间,专门留给我们一家人团聚。星期天就是那个特别的日子。
专为两人和五人设计的自行车
我父亲二十出头的时候(1936年),他和一位朋友一起…… 岛法国他们乘坐一艘大型远洋客轮,从纽约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们买了一辆双人自行车,一起骑行游览了法国,然后又去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结束这段旅程后,我父亲回到家,把自行车带回了布朗克斯的家,供我们全家享用。
我们星期天的早晨通常以从当地犹太熟食店买来的百吉饼、奶油奶酪、熏鲑鱼、腌黄瓜和熏白鱼开始。然后,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会跑到地下室,那里存放着那辆神圣的栗色双人自行车。
我父亲对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做了一些改装。他加装了几个座位:一个在前座后面,用临时车把固定住;另一个则临时安装在后行李架上。想象一下:爸爸妈妈骑着车,我们三兄弟——我坐在前座后面,乔恩坐在后行李架上,小鲍勃则蜷缩在前车篮里。
人们会从附近的廉租公寓里鱼贯而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五个骑车去水库椭圆公园。多么美好的景象啊。但请记住,就像水库椭圆公园和我早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自行车的起源故事也有一段黑暗而痛苦的过往。
大屠杀的阴影
1936年,我的父亲莫里斯抵达布达佩斯后,前往几位亲戚家。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一位年迈的犹太店主被一群“十字箭党”的暴徒从街尾的面包店里拖出来,惨遭毒打。匈牙利的右翼“十字箭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其行事作风效仿德国纳粹党,但与纳粹党卫军冲锋队相比,这些暴徒的反犹主义更加恶毒残暴。
我父亲正准备冲过去帮助那个可怜的人,幸好他的亲戚们抓住了他的胳膊,阻止他冲上去。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命令道:“住手!别去!你一定是疯了。他们会杀了你们俩的!”
因此,除了家里的自行车,父亲从旅途中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可怕景象。战争的阴影早已笼罩在地平线上。伴随其而来的还有纳粹大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以及天主教徒、罗姆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惨遭杀害。
战争和种族灭绝的灾难撼动了世界的根基——也撼动了我的家庭。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除了父亲的父母多拉(昵称“巴巴·多西”)和爷爷马克斯之外,我父亲这边就没有其他在世的亲戚了。这让我格外不安,因为母亲这边,我不仅有外祖父母,还有姑姑、叔叔、堂表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除了一个堂兄之外,父亲在欧洲的所有家人都被纳粹杀害了。
重聚:幸存者内疚
战后,大约在1952年,红十字会开展了一项计划,旨在帮助难民与居住在美国的亲属团聚。他们设法找到了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的年轻人,他已经在森林里生存了两年,像动物一样靠浆果、树根和树叶为生——他是“森林中被遗忘的犹太人”之一,或者正如我所说,“森林犹太人”。
我和父母、祖父母一起去拜访了泽利格,他是我远房表兄,也是我在欧洲唯一一位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父系亲人。我至今仍记得他前臂上纹着的蓝色数字,以及他那神秘莫测、几乎听不懂的外国口音,这些都让我难以忘怀。
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泽利格意外来访后不久,我的祖母多丽丝(人称“巴巴·多西”)将她那八十磅重、虚弱不堪且身患癌症的身体抬到公寓的窗台上,从六楼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才明白,她的自杀是对迟来的幸存者内疚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内疚很可能是由泽利格的来访引发的——泽利格是她在世上唯一的远房亲戚。
后来我才知道,这类噩梦般的创伤可以代代相传。事实上,这些内隐记忆痕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影响了我的一些行为,以及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内疚感。
记忆:失而复得?
当我继续帮助客户挖掘他们隐性的——或者说身体和情感上的——感官记忆时,令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些人竟然提到闻到了烧焦肉的刺鼻气味。这尤其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些人中很多都是长期素食者。
当我请他们采访父母了解家族史时,许多人表示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或幸存者。这些客户是否有可能受到父母和祖父母在集中营中遭受的创伤的某种强烈的、具有种族特异性的、跨代传递的影响?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个人记忆的认知,这种解释似乎不太可能。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集中营的气味究竟是如何一代代传递给我的客户的。但最近,我偶然看到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布莱恩·迪亚斯(Brian Dias)进行的一项令人震惊的动物实验。研究人员让一群小鼠接触樱花的香味。我不知道这种香味对它们来说是否像对人类一样令人愉悦,但肯定不是令人厌恶的。然而,实验人员随后将这种香味与电击结合起来。
经过一两周这样的配对后,小鼠只要一接触到樱花的香味,就会极度恐惧地颤抖、发抖,甚至排便。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然而——我很好奇这些科学家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竟然连续培育了五代小鼠。
这些实验的最终结果是,当研究人员将最初那对小鼠的曾曾孙暴露在樱花香味中时,它们仅仅因为闻到这种香味就惊恐地颤抖、发抖,甚至大小便失禁。这些反应的强度与它们的曾曾祖父母(最初接触樱花香味并伴有电击这种非条件刺激的小鼠)的反应强度相当,甚至更强。
这些小鼠对其他各种气味都没有恐惧反应——唯独对樱花香味有反应!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一个有趣结论是,当雄性(即父亲)是最初交配伴侣中接触到条件反射恐惧反应的那一方时,这种恐惧条件反射的传递效果更佳。这种特异性并没有让我感到完全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身经历的大屠杀记忆主要来源于我的父亲。
治愈祖先创伤
关于这种传承的临床问题是:如何帮助我的客户疗愈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祖先创伤?当这些创伤从未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该如何帮助这些人,也包括我自己,从这些令人不安的记忆印记中疗愈?这个问题对于有色人种和原住民来说也至关重要。
当我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些代际传承时 醒来 这个 虎: - 修护治疗 创伤1996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我经常因为提出这些荒谬的观点而受到批评。然而,到了2023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种祖先遗传,甚至通过动物实验破译了某些类型“表观遗传”的分子基础。
最近,我偶然读到一位“老朋友”的著作。早在此类研究出现之前,甚至在我提出关于代际传递的推测之前,他就提出了类似关于祖先影响的观点。卡尔·荣格在他的书中写道: 心理类型,写道:
“自远古时代以来,地球上发生的所有经历都得到了体现。这些经历越频繁、越强烈,它们在原型中就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永远不会真正结束,为什么不会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版权所有2024。保留所有权利。
经出版商许可改编
Park Street Press,是以下出版社的出版品牌: 内在传统国际.
文章来源
书籍:《创伤自传》
创伤自传:一段疗愈之旅
作者:彼得·A·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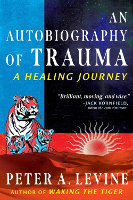 在这本充满个人色彩的回忆录中,著名躯体体验疗法创始人彼得·A·莱文(Peter A. Levine)——他改变了心理学家、医生和治疗师理解和治疗创伤和虐待创伤的方式——分享了他治愈自己严重童年创伤的个人历程,并对他创新疗法的演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在这本充满个人色彩的回忆录中,著名躯体体验疗法创始人彼得·A·莱文(Peter A. Levine)——他改变了心理学家、医生和治疗师理解和治疗创伤和虐待创伤的方式——分享了他治愈自己严重童年创伤的个人历程,并对他创新疗法的演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订购本书, 点击此处. 另有有声书和 Kindle 版本。
关于作者
 彼得·A·莱文博士是著名的躯体体验疗法(Somatic Experiencing)创始人。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与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和国际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荣获四项终身成就奖,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唤醒老虎》(Waking the Tiger),该书已被翻译成33种语言,销量超过百万册。
彼得·A·莱文博士是著名的躯体体验疗法(Somatic Experiencing)创始人。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与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和国际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荣获四项终身成就奖,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唤醒老虎》(Waking the Tiger),该书已被翻译成33种语言,销量超过百万册。
请访问作者的网站: SomaticExperiencing.com
该作者的其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