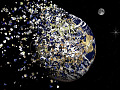昨晚你可能睡了 七到八小时。 其中大约一两个可能是在深度睡眠中,特别是当你年轻或体力活跃时。 那是因为 睡眠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和 行使 影响大脑活动。 大约三四个小时会在浅睡眠中度过。
在剩余时间内,您可能处于快速眼动 (REM) 睡眠状态。 虽然这并不是您的大脑唯一可能做梦的时间(我们在其他睡眠阶段也会做梦),但这是您清醒时最有可能回忆和报告大脑活动的时间。
这通常是因为要么非常奇怪的想法或感觉把你吵醒,要么因为最后一个小时的睡眠几乎耗尽了你的时间。 REM睡眠。 当梦或闹钟叫醒您时,您可能会从梦中醒来,并且您的梦通常会持续到醒来的最初几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记住它。
如果它们是奇怪或有趣的梦,您可能会告诉其他人,这可能会进一步 编码 梦的记忆。
梦和噩梦是神秘的,我们仍在了解它们。 它们让我们的大脑不停运转。 他们在分子水平上清洗了当天发生的事件的想法。 它们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在醒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对快速眼动睡眠和做梦了解多少?
研究梦真的很难,因为人们睡着了,我们无法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 脑成像表明某些 大脑活动模式 与做梦有关(以及与更容易做梦的某些睡眠阶段有关)。 但此类研究最终依赖于梦境体验的自我报告。
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多个目的。
在基本生理水平上(由 大脑活动、睡眠行为和意识研究),所有哺乳动物都会做梦——甚至鸭嘴兽和针鼹也可能经历类似做梦的事情(前提是它们处于梦境) 合适的温度)。 他们的大脑活动和睡眠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一致 REM睡眠.
进化程度较低的物种则不然。 一些 海蜇 – 没有大脑的人 – 确实会经历生理上可被称为睡眠的情况(通过他们的姿势、安静、缺乏反应能力和在提示时快速“醒来”来表现)。 但他们并没有经历与快速眼动梦境睡眠相同的生理和行为要素。
对于人类来说,快速眼动睡眠被认为在夜间每 90 到 120 分钟周期性发生一次。 它可以防止我们睡得太沉 容易受到攻击。 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做梦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变得太冷。 我们的核心体温通常是 做梦时更高。 通常更容易 从梦中醒来 如果我们需要对外部提示或危险做出反应。
快速眼动睡眠中的大脑活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暂时运转起来。 它就像一个进入更清醒状态的潜望镜,观察水面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一切顺利则返回到海底。
一些证据表明,“发烧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常见。 我们实际经历 快速眼动睡眠时间少得多 当我们发烧时——尽管我们所做的梦往往是 色调更深,更不寻常.
当我们发烧时,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可能会减少,因为我们在这个睡眠阶段调节体温的能力要差得多。 为了保护我们,我们的大脑试图通过“跳过”这个睡眠阶段来调节我们的体温。 天气炎热时,我们的梦想往往会减少 为了同样的原因.
大脑深层清洁系统
研究表明,快速眼动睡眠对于确保我们的大脑正常工作非常重要 脑电图,测量大脑活动。
同样,深度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体力,梦睡眠”反冲洗“我们的神经回路。 在分子水平上,支撑我们思维的化学物质会因一天的认知活动而变形。 深度睡眠是指这些化学物质恢复到未使用状态时的状态。 大脑是“洗”与脑脊液,由 淋巴系统.
在下一个层面上,梦境睡眠“整理”我们最近的记忆和感受。 期间 REM睡眠,我们的大脑巩固程序记忆(如何完成任务)和情感。 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通常期望做的梦会更少,这对于巩固情景记忆(生活中的事件)很重要。
随着夜间睡眠的进行,我们会产生更多的皮质醇 - 应激激素。 人们认为皮质醇的含量会影响我们正在巩固的记忆类型,并可能影响我们所做的梦的类型。 这意味着我们晚上做的梦可能是 更加支离破碎或者怪异.
两种睡眠都有帮助 巩固 当天有用的大脑活动。 大脑还会丢弃不太重要的信息。
随意的想法,重新整理的感受
这种对一天活动的归档和丢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梦见发生的事情 白天.
有时,当我们重新整理想法和感受时,要进入“箱子” 在睡眠期间,我们的意识水平使我们能够体验意识。 随机的想法和感受最终以奇怪而奇妙的方式混杂在一起。 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可以解释我们一些梦的奇怪本质。 我们白天的经历也会助长噩梦或充满焦虑的梦。 创伤事件.
有些梦似乎 预言未来或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 在许多社会中,梦被认为是通向现实的窗口。 替代现实 我们可以设想什么是可能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对做梦睡眠的体温调节、分子和基本神经方面的科学理解是 非常好。 但梦的心理和精神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藏的。
也许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尝试理解事物。 人类社会一直在解释随机性——鸟儿旋转、茶叶和行星——并寻找 意。 几乎每个人类社会都认为梦不仅仅是随机的神经放电。
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魔法的东西后来可以被理解和利用——无论是好是坏。![]()
关于作者
德鲁·道森,阿普尔顿研究所所长, 澳大利亚大学 和 玛德琳·斯普雷瑟,心理学讲师, 澳大利亚大学
书籍意识